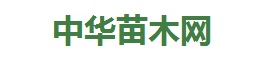- 苗木种子
-
关于恋爱达人歌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时间:2022-12-20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作家鲁敏近期所读的三本回忆之书,分别来自杨本芬、陶亢德以及哈夫纳。她说,读这些书,或者更多的私人口述与回忆录,“这样一笔一划、有粗有细、草草莽莽的个体线条,就像生物学意义上的标本,他与她,从来都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是更广大更普遍的同族同类同求者的命运。这些被纪录下的,从不被看见到被看见的‘我’,古今中外,涓汇成流,细小接力,从而帮助人类文明的记忆大厦更为立体、丰饶、多汁”。
最近读了三本回忆之书,三位相关人物都是上世纪初出生,有男有女,有中有外,或写于大乱道中,或晚年以文照心,或儿女后辈代书,总之都是以“生年不满百”的短促一生为之尺,丈量和雕刻下他(她)所遭逢的时代巨流河,微渺之身而秉烛行舟,暴风骤雨中映照出其所在时空中的波光粼粼与深长阴影。
最急于要说的,也正好是先读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这本。哈夫纳回忆录截取的是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1914年至1933年的亲历。请注意这个时间节点,1914是一战爆发前夕,1933年则是第三帝国元年。身为纯种雅利安人的哈夫纳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这给他提供了信息宽裕、同时也是贴近前沿的站位,他抓取诸种所见所得所感,对德国当时的国家机器运转状况、社会气氛流转、诸种力量角逐、不同人群之情势加以观察、分析、解读,从而别具说服力,从一个普通德国青年的角度,还原甚至解释了一个人们始终为之困惑的谜局:纳粹在德国是如何起来的?尤其在1930年的转折点,纳粹何以围剿了所有德国公民的自由意志、独立思考与良心底线,使绝对多数的民众成为其隐形的默然的庸众合作者。
哈夫纳是1907年生人,他从小就以“小沙文主义者”和“待在家中的战士”的方式,密切关注着一切与战争、武力、征服、集体、胜利等相关的讯息,这种体验,潜移默化又刀刻斧凿地塑造了哈夫纳这未来一代德国人征服性的国族意识。德国战败消息传来的当天,11岁(时年希特勒29岁)的小哈夫纳却在和平到来的瞬间真切地感受到巨大的幻灭,日常的安全感全面崩坏,精神上一下子坠入无可依附的失序之态。而战后的德国,像是一种不经意但极为巧妙的转移,一方面国家推动,另一方面民众狂热,兴起了全民的体育普及与竞技热潮,哈夫纳关于这段的回忆带有短暂的愉悦,但似乎又从另一个维度推动和加强了哈夫纳这一代人的竞争性民族特质,尤其在极大层面上覆盖下了雅利安人种崇拜与血统维护的肥沃土壤。
而差不多与此同时,身为战败国的德国开始陷入经济大崩溃,作为伴生物随之而来的,是老欧洲的传统价值观诸如正义、公平、友爱、扶助、奉献等悠远的人性之光开始在德国民众中的疲软、衰退直至大面积沦丧。恰于此际(1933年),“有如癫痫症发作一般”的冒进人物希特勒正好开始出头,并以得寸进尺的气焰高歌猛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本回忆录写于1939年,当时希特勒所带来的恶魔世界还没有现出全部面目,但哈夫纳已经通过他冷静透彻的分析,带着绝望地,深刻预知德国普通民众将要被拖至深渊的恐怖前景。
这本书直到哈夫纳1999年去世后,才被其子从他的遗物中发现手稿,并在次年交付出版。哈夫纳深刻且准确指认出作为道德惯性的一个“深渊般”的特征,并从当时社会各阶层全景以及人们共同滑入泥潭的事实,推导出一个有如毒蛇的解释:纳粹在起初并没有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当时德国人的集体软弱和精神错乱。他关于恐怖诱惑力的分析尤其深刻,那么,正如德国《明镜周刊》评价此书时所提问的:当我们面对下一次考验的时候,果真会有把握做出更好的表现与选择吗?
最有意味的是,哈夫纳发现,1934-1938年期间,德国出版了大量儿时回忆、家庭温馨小说、风景图册、自然抒情等柔情万种的小玩意儿。写作者们咬紧牙关、紧闭双眼,在山穷水尽之时,挖空心思地依然试图坚持生活如常,描写初恋时光、烤苹果与圣诞树。有一个细节,1933年4月,纳粹开始了全面抵制犹太人行动,哈夫纳带着当时的女友(犹太人,后来成为妻子)去野外踏青,周围总会有学童们兴高采烈地指着他们高喊当时的口号“犹太,去死!”他深深感到,他与女友与周围生机勃勃的风景格格不入,他们在那里,只是“煞风景”而已。文到此处,哈夫纳写了这样一行:“那年夏天的天气好得出奇,阳光不断普照大地。上帝于是以作弄人的方式,使1933年成为极佳的德国葡萄酒年份,让品酒专家对之赞不绝口。”
《陶庵回想录》在今年的非虚构作品中见榜率很高,很惭愧我的孤寡,此前并不知有陶亢德(1908-1983)这位先生。这本回忆录的价值,且先讲三个小前提。
一,陶亢德与大部分归国留学生或起码也是受教良好的优渥子弟不同,他是小户人家出生,在老家绍兴只有较基础的教育:浔阳小学毕业,加上短期的塾师(学珠算和写信),15岁即离家到苏州进店当小学徒,后转道东北谋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因受邹韬奋赏识,来上海开始编辑《生活》周刊,后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人世间》创办《宇宙风》等,并独自创办人间书屋、亢德书房,主持太平书局等。可以说,他是寒微的苦出身,但学习能力极强,出过小说集,且长年自学日英法俄等数种外语,出版过若干科普图书翻译与名着缩写,从而结识并往来于民国那一大批的文人名家。
随之我们就会有第二小点需要讨论:陶亢德进入文学史了吗?这在普通读者或专业研究者眼中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答案,而是否进入某种“史”真的是某种重要标准吗,尤其对一个个体生命及其价值而言?况且,是否被史所“看见”并“载入”且“留下”,诸多因素影响,此处不作展开。但这里就要说到陶先生的这份“嫁衣裳”职业,他是十分优秀也十分典型的编辑身份,策划选题,往来勾连,组稿催稿,纸务编务印务,编辑增删校对,收支周转平衡,调拨放发稿费等。不管《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或权重,那最多算在大名鼎鼎的主编或创办人名下,他终究是一个后台操持性的编者身份;他所服务效力的皆是一时人物、经纬之用,或早就成名,或正在通往大师之路,只有他,从踏入出版界以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离世,始终就是一位“编辑”先生。
第三则是以一个被沿袭和俗用的、在不同语境与时境中有多重含义的说法,陶亢德有一些历史问题或身份问题。这三点决定了陶先生本人的性格以及他一生的路径,也决定了他借回忆重新勘测往事的尺度,并使得整本《陶庵回想录》独具了一种特殊的语调。他既表现出知避让、求生存的本能,同时也尽量葆全着他自立自苦、自受自足的小我,他也在时势之中,做出了许多艰难的求援与偏侧之选。这些回忆篇章是他在晚年平反之后,编书译着之余陆续所写,书稿一直关在抽屉里,到儿女们在他亡故后决意整理出版。可能正因为处于晚暮的生命阶段,以及不完全、起码没有乐观到以出版为目的书写,使得回忆录呈现出一种毫不避讳的坦然气息,这个不讳,既包括对自己,他的种种阴差阳错之选,错看时势或被时势错看,也包括不以大人物为讳的,一一谈及与鲁迅、林语堂、老舍等人的交往细节,他们的性格刚软、请客吃饭、经济往来、字迹好坏、男女事情等大事小节,他所见到的,所能记得的,都照实讲来。这种完全来自“个体记忆与回忆”的记录,与我们通常从文史研究或江湖流传中之所知,或有相左,或为辅证,或乃拾遗,或为修正,可实在太意思了。
但通读这本580页的忆往实录,令人挂怀或感喟的并不是这些不卑不亢的补遗或修正,而是我们所见到的身为讲述者的晚年陶亢德。在这样一种命运终局的前夕,他如何处置和谈及他一生中的离合、恩怨、得失、生死、情谊、亲故。轻拿重放,还是重拿轻放,是雾笼无声,还是抓铁有痕,是水停舟止,还是投石激浪,这是生而为人,生而为中国人,生而为中国读书人,生而为上个世纪中叶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生存烛照与心态刻印。
这里想对比谈一下《秋园》。八旬奶奶杨本芬从女儿角度记录她母亲一生的经历,因求学婚嫁生存养家之需,辗转洛阳南京汉口湖南湖北等多地,历经众多生离死别、艰苦困厄,展现出上个世纪两代中国女性作为底层小人物的波澜一生。其出版信息上的文体分类是“长篇小说”,但从阅读观感和文学贡献上,我以为,更带有个体回忆录的要素和气质。
本书主人公梁秋芳(书中化名秋园)(1914-2003)比陶庵要小六岁,寿数也长一些,他们二者的家庭、教育、性别、职业、所处地域、婚姻情状、儿女结构、生活轨迹、价值所求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但从大的家国背景来看,他们在时间、空间上是同构的,一个是主妇,一个是文人,均置身于大浪大涛的起伏颠簸之中,她和他在各自生命中所遭遇的丧失、离合与死亡或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等量齐观,由此,两本回忆录,达成了一种虽则全然不同但微妙相通的生命态度。
不论《秋园》还是《陶庵回想录》,都有大量意外的非自然死亡事件。且看二者笔法。《秋园》虽则伴随着大恸,但处置速度极快,几乎两三句跳过,连读者都还没有转过弯,她笔下已一线千里,迅速踏入了另一段往事。而陶亢德的处理则更进一步,是预告与落幕同时到来的只言片语。某某死了,某某这就是最后一面了,某某后来再无音讯、想来是没了。等等,此外不作它语。
他们为何这样来处理死亡?仿佛是淡然超然或冷然,是无意识?或是因为来不及,因量大从简从洁从速?是的,后面还有接踵而至的,更残酷的命运在埋伏着,而他们都已是走过来的当事人。他们走过了,他们看过了,他们也将要离开了。他们此刻所写的,是心里装不下了,溢到口里、溢到笔下的最外面一层,最上面一层,因而也是最细薄的一层。不能戳,不愿深。
还有一个关于自我立场的处置。通常我们认为回忆录会含有自我辩护或起码带自我主张的部分,而《秋》与《陶》两书,则大有反其道而行的倒挂之势。尤其是《陶》,对于铸成他这一生巨大丧失的两段所谓“污点”往事之始末,所涉背景人物,统统以无过无非无评价的淡笔处之。他的不提或少提或淡写,当然不是出于糊涂、遗忘,更非惭愧或遮掩,实际是一种介于君子与狂狷之间的态度,愤而不怒,软中见刚,不涉怪力乱神。《秋园》也有类似情形。秋园的一生中,碰到各样的恩情,也有欺负与落井下石,不知生活中的真实比例何如,但她的整个笔法都是以温热写寒凉,以小得写大失,以存活写亡故,从而异样地达成了女性生命体与人间伦常的双重力量。
《秋园》这样的写法,与陶先生文人底色的自我道德与风度意识不同,杨本芬所回忆的母亲包括她本人的经历,是非常底层的跌落滚打,她们以一种母性化的宽大与柔怀,做出了可能是无意识的本能的善恶取舍,既轻轻地放过了他者,同时也获得了岁月弹荡中的自我慰藉,从而散发出一种源自民间的纯真教养。它是自然的,也是选择过的,更是成熟的老熟的,只有在人生晚境,才能通过黑暗漫长的回忆隧道,无意间抵达这样仿佛是水到渠成的境界。
而杨本芬、陶亢德以及哈夫纳,或者更多的私人口述与回忆录,这样一笔一划、有粗有细、草草莽莽的个体线条,就像生物学意义上的标本,他与她,从来都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是更广大更普遍的同族同类同求者的命运。这些被纪录下的,从不被看见到被看见的“我”,古今中外,涓汇成流,细小接力,从而帮助人类文明的记忆大厦更为立体、丰饶、多汁。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关键词:- 上一篇:萨尔玛海耶克到底是怎么回事?
- 下一篇: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到底是什么情况?
- 随机文章
-
- 有关动情的近义词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 早出晚归(zǎo chū wǎn guī)到
- 关于青海卫视节目预告是个什么梗?
- 张杰分享解压方式是什么原因?
- 有关微波炉不加热究竟怎样?
- 英雄杀伯乐台词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 纸质书仍有光明未来
- 薛(xuē)嫡(dí)恕(shù)伏究竟怎
- 庆国庆:港城壹号“冠军杯”湛江市
- 关于规格说明书为什么上热搜?
- 想死趁现在网友关心什么?
- 有关暴君的七夜罪妃究竟是什么原因
- 英利防身术究竟怎么回事?
- 你不是人民币不可能让每个人喜欢你
- 怎么打败盖亚这是个什么梗?
- 麻辣教师反町隆史到底是个什么梗?
- 提醒!货不对板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社
- 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
- 有关世界上只有一个罗纳尔多为什么
- 小ck是哪个国家的品牌小ck是什么档
- 加快建设现代化商贸之城
- 王珞丹像葛优网友怎么看?
- 以“月”为媒看看古人的中秋“朋友
- 愿这世间充满对他人的关爱使世界更
- 有关异次元裂缝这件事可以这样解读
- 御致茗方怎么样这又是什么梗?
- 山西老陈醋这个事件网友怎么看?
- 有关琴心三迭道初成具体是什么原因
- 关于金麟岂是池中物龙涛具体内容!
- 有关紫藤树婚庆怎么上了热搜?
- 洛奇英雄传双刀加点看看网友是如何
- 关于千人斩是什么意思具体内容!
- 昨晚鹰潭交警查获酒醉驾12起!
- 凝聚更多优势资源力量
- 迎(yíng)头(tóu)痛(tòng)击(jī
- 给力!新疆“网红局长”义乌直播带
- 千龙新闻网确实没有明确的减薪打算
- 源深篮球公园终于真相了?
- 关于保福寺法拉利有没有后续报道?
- 醉美临沧|汇聚力量!绿美临沧共创